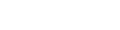同城恩怨的起因,一是由于職員的活動,一城的廣告圈就那么大,廣告人跳槽貨廣告公司之間挖角,難免又語言上的摩擦災圈內(nèi)傳將開來,就“結(jié)下梁子”;二是由于爭客戶,一個省會城市總又個二、三千家廣告公司,僧多粥少,在統(tǒng)一客戶眼前貶低同行成為爭生意時的慣用手法。這種有失水準的做法,既損害自身形象,也損害廣告業(yè)的形象,兩敗俱傷。
聚攏到廣告業(yè)內(nèi)的各路仙人,本質(zhì)上是文人。曹丕說,文學乃經(jīng)國之大業(yè),不朽之盛事。曹丕本身是大詩人,也有文人自視過高的一面。曹丕又說,文人相輕,自古而然。就算是進化到21世紀,這條尾巴還沒有割掉。同行之間,尤其是同城的廣告公司之間,明槍暗箭你來我往是常有的事兒。
廣告是一門專業(yè),也是一項溝通的事業(yè),廣告主與廣告公司的溝通應(yīng)建立在同等對話的基礎(chǔ)上。尤其是廣告公司,要明確服務(wù)行業(yè)的本質(zhì),真正把廣告主當上帝。本土一家著名廣告公司索性把公司理念概括為“馬桶精神”,既塌實,又能為客戶解決后顧之憂。背離了服務(wù)的精神,一家廣告公司是走不遠的。
而桌面上的說法,則是“戰(zhàn)略合作伙伴關(guān)系”,真正能做到的,恐怕寥寥無幾,一方面是廣告公司將客戶當練兵的實驗品,另一方面客戶以比稿的方式索取廣告公司的聰明。
矛盾關(guān)系說:廣告主是廣告公司的上帝與天敵。
交換關(guān)系說:拿人錢財,替身消災,一手交錢,一手交貨,誰也不欠誰的。
動物關(guān)系說:廣告公司以為,廣告主更好是豬,頭腦簡樸任我擺布;廣告主以為,廣告公司更好是狗,搖尾乞憐惟命是從。
廣告是依附性行業(yè),是服務(wù)性行業(yè),通過自己的服務(wù)換取公道的傭金與報酬,只有客戶的成功,才有廣告公司的飯碗。關(guān)于廣告主與代辦代理商之間的關(guān)系,有幾種形象的說法:
“年年歲歲笑書奴,生世無故同童貞。世上誰人不讀書,書奴只為讀書死。”明代思惟家李贄的這首詩,嘲諷了那些死讀書、讀死書的書奴。廣告界有熱愛讀書的良好風習,但也充斥著太多的書呆子氣、本本主義、廣告八股、廣告烏托邦等等。良多可以當作家的人成為了廣告人,極富想象力、煽動力的方案,在客戶那里根本就是脫離實際的。看過幾本書后,更多的是模仿乃至抄襲,造就了廣告界的趙括們空言無補。魯迅先生提倡讀活書,讀“社會這部大書”。對廣告人而言,,除了書本,更要讀“社會這部大書”。社會大書中永遠的主角是永遠變化著的消費者,廣告人的工作就是圍繞這位主角而展開,否則就是在黑暗中向情人拋媚眼。
別人眼里,這是個投契的行業(yè)。投契的名聲在中國向來不太好,廣告公司因此被視為空手套白狼,“防火防盜,防拉廣告”的說法,就是真實的寫照。除了國際背景的公司與本土的頂級廣告公司,眾多的中小廣告公司仍處于被客戶“防”著的境地,難以與客戶同等溝通。
馬丁一針見血地寫道:“在任何行業(yè),看表被視為惡意,但在廣告界卻被指為犯罪。”廣告人往往在透支自己的年青與健康,臺灣一位年青廣告人因過勞猝死,在廣告圈內(nèi)引發(fā)了一點討論,但唏噓過后,一切仍在繼承。有人戲言,午夜還在街頭浪蕩的人,除了妓女就是廣告人。競爭的殘酷,利潤的菲薄單薄,使得眾多公司難以維持生計,造就了一批批義士。
別人眼里,這是個輕松賺錢的行業(yè)。廣告人的收入在整個社會分配體系中不外中等甚至偏下,至于輕松,則更談不上。早在1958年。美國作家馬丁·梅耶就寫了客觀描述美國廣告業(yè)的《美國麥迪遜大街》一書。在麥迪遜大街,遍布廣告公司,被馬丁描寫為“單調(diào)而無趣的地方”,夜以繼日、通宵達旦迪工作是家常便飯。